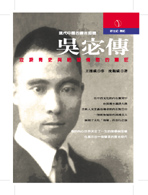
〈宓的保守情〉
所皆之,的五四其是包含了新文化、新文、新潮流的一代,在代,新、代,激保守就像火水一,互不相容、互相解、互不妥──解往往又生更多的。
一九一六年胡起文、一九一七年表〈文改良〉、提倡「文的,的文」以,因秀等人的推提倡,白文的用在五四之後更加普及普遍,早在之前,文言和提倡白的文人者分大,在人才出也壁分明(1),互相反,有人持己,不容他人之反、有人放即使方「羊酒、璧,捧著「白歪」投降」也不收受。
宓正是派的一人物,作《衡》主要大,宓在文化思想上是胡秀等人立的,他胡的八不主乎都不同意,只要的人是胡,他就反,所以他在〈今日文造之正法〉一文中提出文的度主(了反胡的法)、同期亦在日表示新文「其流毒甚大,而其不值通人一笑。」
《衡》刊於一九二二年一月,初始以每月一期方式行,一九二七年中局因售不佳、累甚,定停刊(2),然而在宓梁超忙之下,一年後,不改以月刊、一年六期方式行,後又受因於「友」的不、、境力等外患,以致於行、停停,於在一九三三年七月束了悲欣交集的《衡》。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「my life is a complete failure」──是他在一九四0年自己二十年的人生,「每一事似皆值得作,且皆立意甚高,而以全力赴之,然其果不失。」
大的疙疙瘩瘩,其就是一「新」「」的角力,宓、胡先、梅光迪等人,胡秀等人的主毋就是「叛逆」「端」,他胡的度,就是「攻乎端,斯害也已」了,文只是一始,派的至此燃,文到史、思想、文化,再方法到政治的批建。我必承,在新文的代用「」的形式去、以「」的方式去思考,影力果竟是有限度的,登高而招而呼需要的是代的潮流遇,保守派《衡》、文言一,在那代、潮流遇都有降到他身上,或者是,早在他身上太久了、他下了,史的巨在前、潮流也在改,他力、也一所能,只能以回眸的去作史的守望,文化的走向究不是底的人所能控制。
作一文化的派,宓在他的事(思想)上,潮流立是而易的。可是在情上,他又勇於追求、、浪漫成性,恰恰的保守念生突,心一是宓的第一妻子,另女人毛文此正她的表哥朱君毅在一起,只是世事年料,人人都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候,想、或早在───希望是渺茫。朱君毅、毛文二人解除婚後,已心一婚的宓才:原他深的女人不是她,而是毛文。
「情是魔的惑,加以抵制。」
「情是一疾病或病,只能在沉默中忍受。」
「情是幸福,是上帝的恩、是光,量享受,即使牲自己也在所不惜。」
「情只不是激情欲望,用略金足情,另一方任可言。」
以上是宓日中他於情的看法,我可以,的看:烈、快、、激情、欲望、自私、酷、金、任,其都可以算是情的值本,把情化或大化的人,其才是不懂情的人,以代的看,宓的理解有太大的,只是真正的徵在於,作一文化思想的保守派、作一反「新」的「派」,在民保守、道德仍是必的代,喜新、求新是否算是一矛盾?算不算是自打嘴巴?甚至是不道德?(3)
情她的附加值既然如此,便在於我的方式,是理性近似於冷、是感性以言喻的浪漫、又或者以始,以、甚至其它?新文化代言人胡亦曾面曹英江冬秀的抉,情的值超其它(社地位、名),他一度曹英,但被江冬秀的威而停止──而宓呢?他似乎有太多的力跟的痛苦,毅然然心一婚,婚就是了真,而史正告我:日後他的痛苦其不在於婚面的指,而是毛文根本不他。(4)
可想而知,宓的婚受到多方面的指,主要在於宓作一提倡道德教的大,行依反覆、法以身作,在有愧友、把自己多年在派文人建立的共於一旦,好友寅恪就「此事已成悲之形式」,他的生郭斌在信中乾脆建他快心一合,理由是了《衡》、了理想道德事。
於宓事情的念,我不想含糊地以「矛盾」,竟其中涉了性理性的扎,所「作提倡道德教的大」是否就有追求真的利?是否婚就是罪大?以代的看然是否定的,但是在那「新」「」「」「代」立的代呢?又如何呢?
我假,史已告我、宓也早已作了,於扎、矛盾,他在日也作了大量的自剖、自解、自其、自欺也欺人,不自我安慰不是因在合新的差上出困,宓早就在日一再表示,是自己的自由,任何人都干涉,友不能、「新」「」也不能,一如前言,真正的痛苦不自於友社的不解,而在於他上了一不他的人,那是方面的,那是一方面豁出所有、另方面又得不到的,也就是,宓真正的矛盾不在於新,而在於他的人和不他的人。
如情此景的矛盾才是宓痛苦的地方,我想到西班牙作家特加.加塞(Jose Ortega y Gasset)在「」本引康德的:
我在情欲上的感情其不是受到他所的控制,正好相反的是,那象其是被我的激情幻想所孕育,的消逝是因它在始就是一。
宓毛文的情正是如此,可否他深著毛,且了她婚,之後又一心做著她到外婚的,但只是宓的一情、自欺欺人,直到毛嫁了熊希,我才恍然大悟:原宓早在一始就被自己的幻想,於,替他的情下了解。(5)
沈威教授在《回眸衡派》一中曾分析胡宓在「新」「」立上的比,且宓的思想行是不一致的,我一直把者分是很二分法的作法,太粗糙也太不精,如果只是了述的方便那可厚非,可是我必知道的是:所的「代」「」「新」「」其有的分界,胡提倡一子的新文化新文,但同也搞了二十年的水注、整理故,胡死介石曾布褒令,他「洵新文化中道德之楷模,理中新思想之表」,新的模糊混合,其已胡定了位,而且是恰的位置,世事有的新,也有完全的,不止胡、宓、不止那代,其我都在新之、都在激保守游移。
以新理解宓的情是不是恰?又是不是?我的看法是肯定的,更何作一述上的方便,新保守等名的用也是很很必的,不我想我的用法不在於判值(例如哪是好哪是),而在於呈史的突、自我的限扎,竟史的事是:包括宓在的所有友,抱持著提倡道德又婚是自城做法者大有人在,寅恪如此、宓的生亦是如此,其就宓自己都不地想解──然他自己信不信又是另回事了。的解、新的又始生,生了新、新而,突、容、徨、解,夜漫漫路迢迢,不只是宓,是那代大部份知分子的。
可是我如果新的理性感性,只以情的角度看宓的定的,我,情於出的值,表的形式往往不是喜就是悲。
是他所的,也就是他的情。
:
1:所的「人才出也壁分明」,其是意有所指,就以《衡》作者群,寅恪、胡先等人都胡持著不的友,思想的不同有引起明暗的是非或是小作,胸襟的包容大度其正是那代人最大的特徵。
2:於此,宓在日中的法是:「中局已化,其欲停《衡》 破我之主宗旨,必非之故。」
3:其留生成另新、元配的人物大有人在,只是些大都是新文的者,例如迅的包二奶、徐志摩的婚。
4:一九九九年沈威曾在台北向毛文她宓的年情事,毛的回答是宓她的是方面的,宓是一位呆子。(可《回眸衡派》p280)
5:於宓追求毛文之外的女性、以及因得不到毛而作出的行,非本文,此不多述,有趣的人可上〈宓的志人生悲〉一。
考目:
沈威《宓:泣青史望情的狂》
沈威《回眸衡派》
片:沈威《宓》
二00三年四月二日
後:
「」「代」分,如果只是了述的方便,可厚非,但若其立化、二分法,是可的,竟就某些部分,「代」可「」的延,是我年前的想法。如今重看,不能(竟也是目前界比流行的法),但又多一思考:我在理解,是「主」入「客」的去、去重建,在不循的解、在主客交融的程中,究竟是「代」了「」的意?是「」出「代」意?句很像不?句,外部看,代之延,是有的,但若的在理路看,成「」「代」之延,又有何不可?
是不是告我,在理解上,同密不可分,但不止於延,而是指:「代」「」一事?(「在理解上」,是指一方法的分析,「一事」云云,正是指此。然不可以比成「我,之,主客交融,所以我(人)是,就是我(人)」)
二00五年十月二十二日
文章定位:
